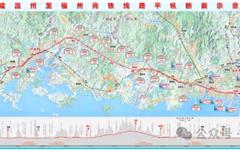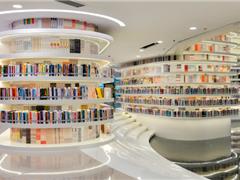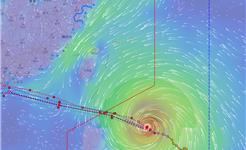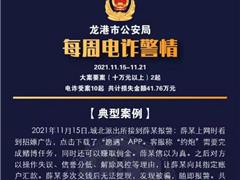温州中学的传达室里放着许多家长带给孩子的滋补品和生活用品。
家里带过来的排骨汤还是热的,
洗衣服、打扫寝室是经常的,
谁让家有高考生呢。
孩子不努力,生气;
成绩上不去,失眠,
过去针对考生的心理辅导,
今年专设了家长专场。
是什么让妈妈焦虑了?
有人说,社会上升通道狭窄,
高考是留给普通大众相对公平的进身之阶。
当高考与社会身份、公平机制捆绑,
高考妈妈的焦虑解药,
又岂是疏通个人情绪那么简单。
龙港网讯 见摄影记者在拍照,温州中学一个高三学生凑上前来建议道:“你们应该在晚上来我们学校的食堂里看看,只有两盏灯亮着,一大群人都在摸黑吃妈妈送来的夜宵, 那场景,真是一道风景!”在温州中学的高三学生眼里,这段时间的黑夜是嘈杂且漫长的。食堂摸黑吃着热腾腾的夜宵,父母们站在一边看着,已经成了他们眼中熟 悉且习以为常的风景。中午,傍晚,校园里随处可见提着餐盒匆匆来去的母亲们。
其实,在家有考生的家长眼中,这段时间的黑夜更是焦虑与煎熬的。 6月4日早上4时多,身在宁波的夏女士在家里蒸好小黄鱼,炖了排骨汤装在饭盒里,拎上电饭锅,坐动车直奔温州,给在瓯海中学读高三的儿子送餐。电饭锅是到 宿舍后热菜用的,保证儿子能吃上妈妈做的热饭热菜。温州南动车站工作人员看她大包小包之外还带个电饭锅,行李实在太多,就帮她拎出车站。
6月5日,高考前两天。天蒙蒙亮,许女士的焦虑情绪发酵到极致,她早上4时就醒了,在家里实在熬不住,不爱运动的她5时多出门跑步。她感觉自己 的弦已经绷得快要断了,跑步时,给好朋友发了条微信,“一直,只有我在努力,而他却一副替我学习的样子。我太辛苦了,生活没意思。”妈妈们的焦虑和非常规 动作,源于一件事——家有考生。记者从市区各中学高三段老师和校心理辅导老师处了解到,面对高考,家长的焦虑情绪一年胜过一年,过去针对考生心理辅导的 “晴朗六月”活动,今年还设了家长专场,心理辅导专场几乎成了诉苦会,家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熬”。被调成了“高考模式”的妈妈,该是怎样一种状态。
“高烤”妈妈
水果热菜送上门洗衣做饭全部包

6月4日下午,是瓯海中学高三学生返校备考的时间,不少家长陪孩子一起返校。在校园里,记者遇到了宁波过来的夏女士,她手里拎着三个袋子,分别 装着水果、衣服、三勒浆。夏女士是泰顺人,在宁波开店,儿子是瓯海中学的高三学生。当天一大早,夏女士从宁波做好菜送到瓯海中学儿子的宿舍后,用带来的电 饭锅把菜热好,看着儿子吃。新衣服是为儿子考试准备的,她担心儿子穿校服,在考试时,会受到考场里一些成绩不好的考生干扰。水果中有儿子爱吃的榴莲,提着 真重,她不得已在学校操场的树荫下休息。夏女士说,她在宁波没心思做生意,就来学校里待着,即便在操场上逛逛做不了什么事情,但离儿子近点,也安心些。
在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就读的儿子升到高三后,许女士向单位请了一年的长假,专职陪读。老师告诉许女士,她儿子是聪明的,如果努力一下,能够考上本科。
可是儿子的第一次模拟考试显示,成绩离本科还有一小段距离,许女士强忍着自己的失望,鼓励儿子:还有时间,我们要一起努力,一定要考上本科。
在到处打听之后,许女士帮儿子找了英语、数学、作文的补习老师。数学老师在永嘉县上塘镇。她透露,儿子高三补习费用过万元,“只要分数能上去,钱就不计较了。”
周末,朋友、同事安排出游,许女士却最忙碌,早上买菜做饭,11时就吃午饭,饭后带儿子马上赶去永嘉学数学。“好老师难找,补习班托了人才进得 去,时间一定要赶上。”周六下午,儿子在补习,她就在外面等着,晚饭在上塘匆匆吃了快餐再赶回市区。周日,又是上午和下午两场补习,晚上,许女士还得把儿 子送回学校。
许女士的三星手机,每天得充两次电,儿子在学校时,她会每天打电话给班主任询问详情,然后再打电话给同学的家长,探探其他同学的状况。许女士甚 至复印了10份儿子的准考证,分别到市区水心殿、妙果寺等寺庙求保佑,她说,一定要去10个寺庙,图个十全十美。连微博微信上看到“传说中的考神”,她也 必定转发一下,求好友祝福。
像许女士这样的专职陪读妈妈,在温州中学附近的“陪读村”也有很多。她们小心翼翼地做着“全职保姆”,包揽洗衣、做饭、洗地、整理被子,不让孩子干一点家务。孩子如果稍微有一点情绪波动,在妈妈看来就是天大的事情。“真是煎熬,快点过去吧。”许女士叹气。
为孩子操心的
八成以上是妈妈

6月4日下午1时许,记者在瓯海中学与该校高三(1)文科班班主任郑小侠谈话,半小时内,有3位妈妈来找郑小侠拿孩子的准考证。郑小侠说,大部分孩子的妈妈,已经不让孩子干除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了,准考证6月3日才到学校,5月底,不少家长就盯着老师要拿准考证。
小余家就住在瓯海中学附近的龙霞路,离学校两三分钟的路程,妈妈舍不得孩子花费这么点时间,跑到学校里帮孩子拿准考证。妈妈说,家楼下开诊所, 怕吵到孩子复习,另外租了一处房子,发现还是不太安静,就又帮孩子租了一个7楼的房间,每到饭点,妈妈就送饭到出租房,孩子不用下楼。
瓯海中学男生宿舍管理人员范师傅说,每周三是家长开放日,来的大多是高三段的家长,高三下学期以来,有半数以上家长每周三必来,八成以上是妈妈。“妈妈可以帮助整理房间,洗衣服。”
难道爸爸就不关心高考生吗?高考生妈妈许女士一说到这个就生气,“好像孩子是我一个人的,他爸爸都不操心,说没关系,孩子长大后自然会懂事,现在不必在学习上死缠烂打。”
郑小侠已经带了十届高三学生,他也注意到,为孩子的事情找他的,大部分是妈妈。“可能家庭分工不同,妈妈更加注重细节,但这对孩子不完全是好事。孩子有时候需要爸爸那种豁达、宽广的胸怀来引导。”
失眠、孤独、生闷气
家长的焦虑赶超考生
温州中学心理辅导老师刘志鹏在接高考心理热线时,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。孩子在家打电脑游戏,妈妈痛心地说,都快高考了,你还打游戏?催促孩子拿 起课本。孩子把妈妈推出房间后,关起门来继续玩。妈妈敲门不奏效,找了师傅,把门拆下来强行进入儿子房间,母子间爆发了一场大冲突,孩子哭着连夜回学校宿 舍。妈妈在家哭了一场后,打电话给刘志鹏诉苦:“只剩这么几天了,他居然还这副德行,想不想考大学了?我的心血都白费了。”
请假一年在家陪读的许女士也会生闷气, “我已经半年不出去和朋友聚会吃饭了。”许女士说,儿子成绩不提高,耽误的可是一辈子,现在本科毕业生就业已经很难,大专就别想找到工作了,没找到好工 作,今后的日子会很艰难。一想到这个,她就焦虑得不行。最近两个月,她失眠、内分泌失调,不得已每周增加了去看中医的行程。
记者从市区各医院的心理科了解到,最近3个月以来,高三学生的家长因失眠来咨询的占了相当一部分,失眠的以妈妈居多。
无论是高三班主任,还是高中段的心理辅导老师,他们一致认为,近些年来,高考生妈妈的焦虑状态越来越严重,程度已经超过学生。温州市第二十二中 学高三段长张崇钗和瓯海中学高三(1)班班主任都说,孩子在高中阶段,学校会潜移默化灌输给孩子正确面对高考的理念和心态,大部分家长却处于疏导无门的状 态。
市教育教学研究院组建了“晴朗六月”考前心理辅导志愿者小组,我市各高校、中学的心理辅导老师志愿参加,“晴朗六月”活动今年已经走到第5个年 头。心理老师针对现状,今年增加了面向家长的“家有考生”辅导专场,在青少年活动中开展讲座,百多名家长报名来听讲座。牵头此项活动的温州中学心理辅导老 师刘志鹏说,现场反馈情况来看,家长比学生压力大。
一是体现在家长期望值过高。比如孩子能考本科的,家长希望考上重点,孩子能考大专的,家长想要本科。但孩子的能力是有限的,与家长的期望有距离,有些家长不愿接受现实,就会产生焦虑,转而表现为对孩子学习加强督促、唠叨、控制不住脾气;
其次是妈妈有强烈的孤独感。很多妈妈反映,她是在孤军作战,孩子没有一起努力,这让她很生气。从小到大,为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课本知识,妈 妈几乎代办了孩子生活中所有的琐事,这样一来,妈妈感觉自己很吃力,而孩子也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,没有体现出感激之情,在关键的高三,如果妈妈没有看到 孩子跟她一样努力,就会有孤独感;
第三是妈妈的生活状态被改变。有的妈妈不工作、不看电视、不开电脑、推掉一切社交活动,只为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复习环境。其实,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,过度约束自己,对于个别不懂得自我排解的妈妈而言,也不是件好事情。
刘志鹏说,毕竟现在独生子女多,家庭容易把所有的希望压在孩子身上,高考对家庭来说是件大事,家长要是没有特别的表现,反倒会被身边的人认为不尽责。家长的种种表现也是能够理解的。
今天起,高三学生进入考试模式,不少家长也同样从备考调整到考试模式,等在校门口,接送孩子,只为图个安心。采访中,大多数家长表示会接送孩子,半数表示要等在考场外面。
考试过后,家长也不敢放松,等分数、选专业、填志愿,还有一道一道的考验在等着他们。高考焦虑是
一种社会病
中国社会高考焦虑症年年发作,年年“精彩纷呈”。
其实,高考狂欢现象不只在中国发生,强调竞争、重视考试的东亚近邻如韩国和日本,也能不时听说如此“盛况”。但在今日中国,让人看着特别不协调 的是,一方面,越来越多的家长早早地把孩子送进国际班甚至直接送出国,以决绝的态度告别高考,彻底摆脱这一系列焦虑;另一方面,留在国内高考的家长和学生 仍然为着大学的一席之地如痴如狂。
按理说,大学扩招多年,适龄人口也在减少,考生及其家长的焦虑状态应该大大减轻,可为什么生活现实呈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幕?
问题其实不在高考本身,而在于当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与高考家庭的特殊心理状态。通常,能够选择摆脱高考的家庭在社会上属于相对“成功”的阶层,家 长本身受教育程度比较高,眼界开阔,对孩子在应试体制下可能遭遇的思维禁锢、性格扭曲和体质下降,有更多的认识和防范。更重要的是,较为宽裕的经济收入不 但可以使他们支付得起孩子国内进国际班或出国念大学的资金,而且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相对平和,对进大学特别是进名校多了些“平常心”。然而,这批家长和学 生的缺席高考仅仅减少了人数的总量,并没有减少社会焦虑的总量,反而容易造成焦虑人员集中,并提高焦虑程度。
按照生活常识,越是部分家庭采取拒绝国内高考的平和态度,越会刺激一部分仍然执著于高考的家庭。因为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之后,中国人早已陷 入难以自拔的相互攀比。越是有实力的家庭不上国内大学,没实力的家庭越是需要拿进入国内名校来与之抗衡——“你们的孩子因为没有实力,才选择漂洋过海曲线 上学的路径,我家孩子不用花那么多钱,还上了名校,比你家强多了!”
生活的残酷在于,如此自我安慰只起到暂时麻醉的作用,其真实效果却是一则加重了自己和孩子必须考上名校的压力,二则反而让自己更明白无论怎么争 强斗狠,对现实也是无可奈何。碍于中国人的面子,如此想法不可能得到坦率的承认,所以只能强行将其封闭进“无意识层面”,最终造成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巨大应 力。应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外部任何一个不利于孩子高考的小刺激,都会成为内心应力宣泄的突破点。作为高考焦虑具体症状的种种小题大做,不过是应力宣泄的表现 方式罢了。
中国高考包括其前身科举考试,都是阶层化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,高考在公平问题上特别敏感,时刻都在提醒国人这一点。然而,一切公平机制都是在越 不公平的场合作用越大。其激发的社会不公平感越强烈,人们追求公平的驱动就越猛烈,对于干扰自身追求的因素之反应也越激烈,由此产生的焦虑程度越不可理 喻。说到这里,谁都明白,解决高考焦虑症应该往哪里对症下药,改革教育体制包括应试模式和考试方式最多不过是辅助手术而已。
顾骏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